凝視死亡:一位外科醫師對衰老與死亡的思索
Being Mortal:Medicine and What Matters in the End
在我們的骨頭和牙齒軟化的同時,身體的其他部分卻變硬了。血管、關節、心臟瓣膜甚至肺,由於吸取了大量的鈣沉積物,從而變得堅硬。在顯微鏡下,血管和軟組織中的鈣與骨頭的鈣是一模一樣的。手術的時候,進入老年人的體內,手指能感覺到其主動脈和其他主血管已變硬並缺乏彈性。研究發現,同膽固醇水平相比,骨密度的降低甚至比動脈粥樣硬化病能夠更好地預測死亡。隨著生命的老化,鈣好像從骨骼滲漏出來,進入了組織。
為了使同樣數量的血液流經變窄、變硬的血管,心臟只得產生更大的壓力。結果,一多半的人到了65歲時形成了高血壓。由於必須頂著壓力輸送血液,心臟壁增厚,對運行需要的反應能力減弱。因此,從30歲開始,心髒的泵血峰值穩步下降。人們跑步的長度和速度都趕不上過去,爬一段樓梯而不喘粗氣的能力也逐漸下降。
心臟壁在增厚,而別的部位的肌肉卻變薄了。40歲左右,肌肉的質量和力量開始走下坡路。到80歲時,我們丟失了25%~50%的肌肉。
眼睛無法視物的原因有所不同。晶狀體是由極其耐久的晶體蛋白構成的,但是,其化學成分會發生改變,隨著時間的推移,彈性會降低——因此,許多人都有的遠視(老花眼)往往始於40歲。這個過程還使得晶體逐漸發黃。即便沒有白內障(由於年齡、過度接觸紫外線、高膽固醇、糖尿病或抽菸等導致晶體白濁混沌),一個60歲健康人的視網膜接收到的光線也只是一個20歲年輕人的1/3。
“主流的醫生會避開老年病,因為他們沒有對付‘老廢物’的設施,”老年病學專家菲利克斯·西爾弗斯通解釋道,“‘老廢物’要麼是耳背,要麼視力差,要麼記憶力有所缺損。為‘老廢物’看病,你得放慢速度,因為他會讓你重說一遍或者再問一次。而且,‘老廢物’不是只有一個主要問題——他有15個主要問題。那你怎麼處理所有的問題?你不知所措。而且,其中有些病他已經得了50年了。他有高血壓、糖尿病或者關節炎。治療其中任何一個病對醫生來說都沒什麼吸引力。”
布魯道告訴我,醫生的工作是維護病人的生命質量。這包含兩層意思:儘可能免除疾病的困擾,以及維持足夠的活力及能力去積極生活。大多數醫生只治療疾病,以為其他事情會自行解決。如果沒有改善呢?如果病人身體衰弱、該去養老院呢?那麼,這似乎並不是醫學問題,對不對?
然而,對於一個老年病學專家,這是一個醫學問題。
老人說,他們怕的不是死亡,而是死前的種種——失聰、喪失記憶、失去摯友,以及不再能夠像以前一樣獨立過活。正如席佛史東告訴我的:「年老是一連串的失落。」菲立普.羅斯(Philip Roth)在描述男性肉體衰老的小說《凡人》(Everyman)中,論道:「年老不是一場戰役,而是屠殺。」
50多年前,社會學家歐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在他的著作《收容所》(Asylums)裡寫到了監獄和療養院之間的相同之處。
療養院和軍事訓練營、孤兒院及精神病院一樣,是“純粹的機構”——在很大程度上是跟社會隔絕的地方。他寫道:“現代社會的基本運轉原則是這樣的:個人在不同的地方睡覺、玩樂、工作,有不同的同伴,接受不同權威的領導,沒有一個總體的理性計劃。”
而純粹的機構則打破了區隔生活領域的屏障,他逐一列舉了具體的方式:首先,生活的各個方面都是在同一個地方、在同一個中心權威領導之下進行的;其次,成員日常活動的各個方面都是和一大群人一起完成的;再次,日常活動的各個方面都是緊密安排的,一個活動緊接著另一個預先已經安排好的活動,活動的整個流程是由一套明確的正式規定和一群長官自上而下強行實施的;最後,各種強加的活動被整合為一套計劃,據稱是為了實現機構的官方目標。
研究發現,年齡大了以後,人們交往的人減少,交往對象主要是家人和老朋友。他們把注意力放在存在上,而不是放在做事上;關注當下,而不是未來。
隨著你的視野收縮,當你開始覺得未來是有限的、不確定的時候,你的關注點開始轉向此時此地,放在了日常生活的愉悅和最親近的人身上。
“文化具有極大的惰性,”他說,“所以它是文化。它之所以能發揮作用,是因為它持久。文化會把創新扼殺在搖籃中。”
1908年,哈佛大學哲學家約西亞·羅伊斯(Josiah Royce)寫了題為《忠誠的哲學》(The Philosophy of Loyalty)一書。羅伊斯關注的不是衰老的考驗,而是一個謎,這個謎對於任何一個思考其必死性的人至關根本。
羅伊斯想弄明白:為什麼僅僅存在,僅僅有住、有吃、安全地活著,對於我們是空洞而無意義的?我們還需要什麼才會覺得生命有價值?
他認為,答案是:我們都追求一個超出我們自身的理由。對他來說,這是人類的一種內在需求。這個理由可大(家庭、國家、原則)可小(一項建築工程、照顧一個寵物)。重要的是,在給這個理由賦予價值、將其視為值得為之犧牲之物的同時,我們賦予自己的生命以意義。
”如果我們看不見內在的光明,那可以試一試外在的光明。”
這裡涉及一個觀念性的基本錯誤。大多數醫生認為,討論絕症的主要目的是決定病人想要什麼——要不要化療,是否希望心臟復甦,是否採用善終服務。我們著力於陳說事實和選項。但是,布洛克說,這是錯誤的。
“主要任務是幫助人們應對各種洶湧而來的焦慮——對死亡的焦慮,對痛苦的焦慮,對所愛的人們的焦慮,對資金的焦慮。”她解釋說,“人們有很多擔憂和真正的恐懼。”
一次談話並不能涉及所有問題。接受個人的必死性、清楚瞭解醫學的侷限性和可能性,這是一個過程,而不是一種頓悟。
布洛克認為,並沒有某種固定的辦法可以引導絕症患者度過這個過程,但是有一些原則是固定的。你坐下來,掌控談話時間。你不是在決定他們是需要A治療方案還是B治療方案,而是想努力瞭解在這種情況下,對他們來說,什麼最重要——這樣你就可以給他們提供信息和辦法,使他們有最好的機會去實現自己的願望。這個過程既要求表達,也要求傾聽。布洛克認為,如果你說話的時間超過了一半,那麼,你就說得太多了。
舊體制的一個美妙之處就是它使得這些決定很容易做。你採用已有的、最積極的治療方法就是了。其實那根本就不是一個決定,而是一個預設項。
公元前380年,柏拉圖在《拉凱斯》(Laches)中記錄了蘇格拉底和兩位雅典將軍的對話。他們想尋求一個看似簡單的問題的答案,那就是,何為勇氣?拉凱斯和尼西亞斯兩位將軍去找蘇格拉底解決他們之間的一個爭端:是否應該教育接受軍事訓練的男孩們戴著盔甲戰鬥?尼西亞斯認為應該,而拉凱斯持相反意見。
蘇格拉底問:“訓練的最終目的是什麼?”
他們認為是培養勇氣。
那麼,什麼是勇氣?
勇氣,拉凱斯答道:“是心靈的某種忍耐。”
蘇格拉底表示懷疑。他指出,有時候,勇敢不是不屈不撓,而是退卻甚至逃跑。世上難道沒有愚蠢的忍耐嗎?
拉凱斯表示同意,但又加了一個定語。也許勇氣是“智慧的忍耐”?
這個定義似乎更恰當。但是蘇格拉底質疑勇氣是否一定和智慧有如此密切的聯繫。
他問道:“難道我們不讚賞追求一個不明智的目標的勇氣嗎?”
拉凱斯承認:“也是。”
這時尼西亞斯登場了。他爭辯說,勇氣就是“在戰爭中或者在任何事情中,知道需要害怕什麼或者希望什麼”。但是蘇格拉底發現他的定義也有問題,因為一個人可以在對未來一無所知的情況下保有勇氣。實際上,個人常常必須如此。
兩位將軍被難住了。故事結尾處,他們都沒有得出最終結論。但是,讀者可能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勇氣是面對知道需要害怕什麼或者希望什麼時體現的力量,而智慧是審慎的力量。
在年老和患病的時候,人至少需要兩種勇氣。
第一種勇氣是面對人終有一死的事實的勇氣——尋思真正應該害怕什麼、可以希望什麼的勇氣。這種勇氣已經夠難了,我們有很多理由迴避它。
但是更令人卻步的是第二種勇氣——依照我們發現的事實採取行動的勇氣。問題在於明智的目標往往並不那麼明確。很長時間以來,我以為這只是因為不確定性。當我們很難知道會發生什麼時,我們就難以知道應該做什麼。但是,我認識到,更為根本的挑戰是:個人必須決定他所害怕或者希望的事項是否應當是最緊要的。
對於人類來說,生命之所以有意義乃是因為那是一個故事。一個故事具有整體感,其弧度取決於那些有意義的時刻、那些發生了重要事情的時刻。
“我們的心智結構內在有一種不一致性,”卡尼曼評述道,“我們對於痛苦和愉快經驗的持續程度有強烈的偏愛,希望痛苦短暫而快樂持久。但是我們的記憶……發展到只呈現一個事件最痛苦或者最愉快的時刻(高峰)和事件結束時的感受。忽視持續時間的記憶不滿足於我們對長時間愉快和短時間痛苦的偏好。”
善終不是好死而是好好活到終點
Being Mortal:Medicine and What Matters in the End
你願意人生最後一哩路,是眼神空洞的坐在輪椅上滑行嗎?
你希望至愛親人的餘生,是靈魂被禁錮在病床上的軀體裡?
人生的終極目標是「好好的活」,有尊嚴地活到最後一分鐘!
重新思考年老生活、安寧照護,到死亡的尾聲
獻給 都會變老的我們
你希望至愛親人的餘生,是靈魂被禁錮在病床上的軀體裡?
人生的終極目標是「好好的活」,有尊嚴地活到最後一分鐘!
重新思考年老生活、安寧照護,到死亡的尾聲
獻給 都會變老的我們
在我們的骨頭和牙齒軟化的同時,身體的其他部分卻變硬了。血管、關節、心臟瓣膜甚至肺,由於吸取了大量的鈣沉積物,從而變得堅硬。在顯微鏡下,血管和軟組織中的鈣與骨頭的鈣是一模一樣的。手術的時候,進入老年人的體內,手指能感覺到其主動脈和其他主血管已變硬並缺乏彈性。研究發現,同膽固醇水平相比,骨密度的降低甚至比動脈粥樣硬化病能夠更好地預測死亡。隨著生命的老化,鈣好像從骨骼滲漏出來,進入了組織。
為了使同樣數量的血液流經變窄、變硬的血管,心臟只得產生更大的壓力。結果,一多半的人到了65歲時形成了高血壓。由於必須頂著壓力輸送血液,心臟壁增厚,對運行需要的反應能力減弱。因此,從30歲開始,心髒的泵血峰值穩步下降。人們跑步的長度和速度都趕不上過去,爬一段樓梯而不喘粗氣的能力也逐漸下降。
心臟壁在增厚,而別的部位的肌肉卻變薄了。40歲左右,肌肉的質量和力量開始走下坡路。到80歲時,我們丟失了25%~50%的肌肉。
眼睛無法視物的原因有所不同。晶狀體是由極其耐久的晶體蛋白構成的,但是,其化學成分會發生改變,隨著時間的推移,彈性會降低——因此,許多人都有的遠視(老花眼)往往始於40歲。這個過程還使得晶體逐漸發黃。即便沒有白內障(由於年齡、過度接觸紫外線、高膽固醇、糖尿病或抽菸等導致晶體白濁混沌),一個60歲健康人的視網膜接收到的光線也只是一個20歲年輕人的1/3。
“主流的醫生會避開老年病,因為他們沒有對付‘老廢物’的設施,”老年病學專家菲利克斯·西爾弗斯通解釋道,“‘老廢物’要麼是耳背,要麼視力差,要麼記憶力有所缺損。為‘老廢物’看病,你得放慢速度,因為他會讓你重說一遍或者再問一次。而且,‘老廢物’不是只有一個主要問題——他有15個主要問題。那你怎麼處理所有的問題?你不知所措。而且,其中有些病他已經得了50年了。他有高血壓、糖尿病或者關節炎。治療其中任何一個病對醫生來說都沒什麼吸引力。”
布魯道告訴我,醫生的工作是維護病人的生命質量。這包含兩層意思:儘可能免除疾病的困擾,以及維持足夠的活力及能力去積極生活。大多數醫生只治療疾病,以為其他事情會自行解決。如果沒有改善呢?如果病人身體衰弱、該去養老院呢?那麼,這似乎並不是醫學問題,對不對?
然而,對於一個老年病學專家,這是一個醫學問題。
老人說,他們怕的不是死亡,而是死前的種種——失聰、喪失記憶、失去摯友,以及不再能夠像以前一樣獨立過活。正如席佛史東告訴我的:「年老是一連串的失落。」菲立普.羅斯(Philip Roth)在描述男性肉體衰老的小說《凡人》(Everyman)中,論道:「年老不是一場戰役,而是屠殺。」
50多年前,社會學家歐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在他的著作《收容所》(Asylums)裡寫到了監獄和療養院之間的相同之處。
療養院和軍事訓練營、孤兒院及精神病院一樣,是“純粹的機構”——在很大程度上是跟社會隔絕的地方。他寫道:“現代社會的基本運轉原則是這樣的:個人在不同的地方睡覺、玩樂、工作,有不同的同伴,接受不同權威的領導,沒有一個總體的理性計劃。”
而純粹的機構則打破了區隔生活領域的屏障,他逐一列舉了具體的方式:首先,生活的各個方面都是在同一個地方、在同一個中心權威領導之下進行的;其次,成員日常活動的各個方面都是和一大群人一起完成的;再次,日常活動的各個方面都是緊密安排的,一個活動緊接著另一個預先已經安排好的活動,活動的整個流程是由一套明確的正式規定和一群長官自上而下強行實施的;最後,各種強加的活動被整合為一套計劃,據稱是為了實現機構的官方目標。
研究發現,年齡大了以後,人們交往的人減少,交往對象主要是家人和老朋友。他們把注意力放在存在上,而不是放在做事上;關注當下,而不是未來。
隨著你的視野收縮,當你開始覺得未來是有限的、不確定的時候,你的關注點開始轉向此時此地,放在了日常生活的愉悅和最親近的人身上。
“文化具有極大的惰性,”他說,“所以它是文化。它之所以能發揮作用,是因為它持久。文化會把創新扼殺在搖籃中。”
1908年,哈佛大學哲學家約西亞·羅伊斯(Josiah Royce)寫了題為《忠誠的哲學》(The Philosophy of Loyalty)一書。羅伊斯關注的不是衰老的考驗,而是一個謎,這個謎對於任何一個思考其必死性的人至關根本。
羅伊斯想弄明白:為什麼僅僅存在,僅僅有住、有吃、安全地活著,對於我們是空洞而無意義的?我們還需要什麼才會覺得生命有價值?
他認為,答案是:我們都追求一個超出我們自身的理由。對他來說,這是人類的一種內在需求。這個理由可大(家庭、國家、原則)可小(一項建築工程、照顧一個寵物)。重要的是,在給這個理由賦予價值、將其視為值得為之犧牲之物的同時,我們賦予自己的生命以意義。
”如果我們看不見內在的光明,那可以試一試外在的光明。”
這裡涉及一個觀念性的基本錯誤。大多數醫生認為,討論絕症的主要目的是決定病人想要什麼——要不要化療,是否希望心臟復甦,是否採用善終服務。我們著力於陳說事實和選項。但是,布洛克說,這是錯誤的。
“主要任務是幫助人們應對各種洶湧而來的焦慮——對死亡的焦慮,對痛苦的焦慮,對所愛的人們的焦慮,對資金的焦慮。”她解釋說,“人們有很多擔憂和真正的恐懼。”
一次談話並不能涉及所有問題。接受個人的必死性、清楚瞭解醫學的侷限性和可能性,這是一個過程,而不是一種頓悟。
布洛克認為,並沒有某種固定的辦法可以引導絕症患者度過這個過程,但是有一些原則是固定的。你坐下來,掌控談話時間。你不是在決定他們是需要A治療方案還是B治療方案,而是想努力瞭解在這種情況下,對他們來說,什麼最重要——這樣你就可以給他們提供信息和辦法,使他們有最好的機會去實現自己的願望。這個過程既要求表達,也要求傾聽。布洛克認為,如果你說話的時間超過了一半,那麼,你就說得太多了。
舊體制的一個美妙之處就是它使得這些決定很容易做。你採用已有的、最積極的治療方法就是了。其實那根本就不是一個決定,而是一個預設項。
公元前380年,柏拉圖在《拉凱斯》(Laches)中記錄了蘇格拉底和兩位雅典將軍的對話。他們想尋求一個看似簡單的問題的答案,那就是,何為勇氣?拉凱斯和尼西亞斯兩位將軍去找蘇格拉底解決他們之間的一個爭端:是否應該教育接受軍事訓練的男孩們戴著盔甲戰鬥?尼西亞斯認為應該,而拉凱斯持相反意見。
蘇格拉底問:“訓練的最終目的是什麼?”
他們認為是培養勇氣。
那麼,什麼是勇氣?
勇氣,拉凱斯答道:“是心靈的某種忍耐。”
蘇格拉底表示懷疑。他指出,有時候,勇敢不是不屈不撓,而是退卻甚至逃跑。世上難道沒有愚蠢的忍耐嗎?
拉凱斯表示同意,但又加了一個定語。也許勇氣是“智慧的忍耐”?
這個定義似乎更恰當。但是蘇格拉底質疑勇氣是否一定和智慧有如此密切的聯繫。
他問道:“難道我們不讚賞追求一個不明智的目標的勇氣嗎?”
拉凱斯承認:“也是。”
這時尼西亞斯登場了。他爭辯說,勇氣就是“在戰爭中或者在任何事情中,知道需要害怕什麼或者希望什麼”。但是蘇格拉底發現他的定義也有問題,因為一個人可以在對未來一無所知的情況下保有勇氣。實際上,個人常常必須如此。
兩位將軍被難住了。故事結尾處,他們都沒有得出最終結論。但是,讀者可能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勇氣是面對知道需要害怕什麼或者希望什麼時體現的力量,而智慧是審慎的力量。
在年老和患病的時候,人至少需要兩種勇氣。
第一種勇氣是面對人終有一死的事實的勇氣——尋思真正應該害怕什麼、可以希望什麼的勇氣。這種勇氣已經夠難了,我們有很多理由迴避它。
但是更令人卻步的是第二種勇氣——依照我們發現的事實採取行動的勇氣。問題在於明智的目標往往並不那麼明確。很長時間以來,我以為這只是因為不確定性。當我們很難知道會發生什麼時,我們就難以知道應該做什麼。但是,我認識到,更為根本的挑戰是:個人必須決定他所害怕或者希望的事項是否應當是最緊要的。
對於人類來說,生命之所以有意義乃是因為那是一個故事。一個故事具有整體感,其弧度取決於那些有意義的時刻、那些發生了重要事情的時刻。
“我們的心智結構內在有一種不一致性,”卡尼曼評述道,“我們對於痛苦和愉快經驗的持續程度有強烈的偏愛,希望痛苦短暫而快樂持久。但是我們的記憶……發展到只呈現一個事件最痛苦或者最愉快的時刻(高峰)和事件結束時的感受。忽視持續時間的記憶不滿足於我們對長時間愉快和短時間痛苦的偏好。”
善終不是好死而是好好活到終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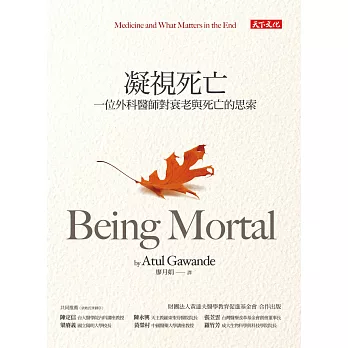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