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機騙局:潛藏在生活與市場中的機率陷阱
塔雷伯(Nassim Nicholas Taleb)的書。
他的《黑天鵝效應》算是幾年前讓我的思考模式大進化的一本好書,後來的《反脆弱》其實比較硬,不是那麼好讀。
《隨機騙局》算是他的成名之作,不過台灣出的是更新二版。
這三部曲建議讀的順序是:《隨機騙局》、《黑天鵝效應》、《反脆弱》。
本書中,機率主要是應用懷疑論的分支,不屬工程學門(儘管數學妄自尊大,喜歡處理這個主題,但是和機率微積分有關的問題,價值只能作為註腳而已)。
怎麼做呢?機率不只用於計算骰子每一面出現的機率,或者更為複雜的變化用途﹔它是指接受我們的知識缺乏確定性,並且發展各種方法以處理我們的無知。
作者的整個事業生涯,都在抨擊機率的計量使用。
本書的觀念是「事情比我們所想的要隨機」,而不是「一切事情都隨機」。
《有錢人想的和你不一樣》指出,他研究最深、超過一千位百萬富翁的具代表性群組,並沒有在他們的童年展現高智力,因此推斷並不是你的天賦使你富有----而是勤奮工作造成的。從這裡,可以天真地推論機運在成功中並未扮演任何角色。
我的直覺是,如果百萬富翁的屬性接近一般人,我會做出更令人不安的解釋,說那是因為運氣發揮了某種作用。運氣是民主的,不管原來的技能為何,都會降臨在每個人身上。作者點出百萬富翁和一般人不同的一些特質,例如韌性和勤勞。這是混淆必要和因果的另一個說法。就算所有的百萬富翁都是執著、勤奮的人,並不會使執著的勤奮工作者成為百萬富翁。
許多不成功的創業家也是執著、勤奮的人。作者在天真經驗主義的教科書個案中,也尋找這些百萬富翁共同具備的特質,並且研判他們都喜歡冒險犯難。冒險犯難顯然是大獲成功的、必要條件----卻也是失敗的、必要條件。要是作者對破產公民做相同的研究,肯定會發現他們也喜愛冒險犯難。
(存活者偏誤)
我們的缺陷是無法修復的,至少就這個環境來說是如此----不過,只有相信理想化人類存在的空想家,才會覺得這是壞消息。目前的思維有以下兩種南轅北轍的人類觀點,它們之間幾乎沒有其他見解。一邊是本地學院的英語教授;二十步快樂術和一星期成為更好的人的秘訣作家。這稱作烏托邦觀點,他們相信合理和理性----我們應該克服路上的文化障礙,成為更好的人類。他們認為我們能夠隨意控制我們的性質,以及只要一聲令下,就能使它轉型,以取得幸福和理性等東西。
另一邊則是對人類持有悲慘觀點,相信我們的思考和行動方式存在與生俱來的局限和缺陷,而且有必要承認這個事實,作為任何個別和集體行動的基礎。否證和不信任知識性的「答案」,實際上等於否證和不信任相信自己確切知道任何事情的人。
這本書的觀念完全落在悲慘類中:我們有缺點,而且不必費心想要改正我們的缺陷。我們的缺憾是那麼大、和環境是那麼不適配,只能繞過這些缺陷過日子。我全部的成人和專業生活幾乎都花在大腦(不被隨機性愚弄)和情緒(完全被隨機性愚弄)之間的激烈爭戰之後,相信我唯一成功的地方,是繞過我的情緒,而不是去將它們合理化。努力設法擺脫人性,或許不可行:我們需要運用一些計謀,而不是依賴某種堂而皇之的道德勸說。
來談一下人的情緒表現。幾乎沒人能夠隱藏自己的情緒。行為科學家相信,成為領導人的主要理由之一,不是來自他們表面上擁有的技能,而是他們透過很難察覺的身體訊號----例如我們現在所說的「感召力」----給別人留下極其膚淺的印象得來的。這種現象的生物層面,目前在「社會情緒」的主題下,很多人投入研究。在此同時,有些歷史學家可能會以戰術性技能、合適的教育,或者事後見到的其他某種理論性原因,「解釋」人何以成功。
賭俄羅斯輪盤賺來的一千萬美元,和勤快而技巧熟練的牙醫執業賺得的一千萬美元,價值不同。它們的金額相同,能買到相同的產品,但其一對隨機性的依賴大於另一。不過,在會計師看來,它們完全相同。你的鄰居也覺得它們沒有兩樣。
我們的腦袋瓜子不是為了了解機率而設計的。
資訊提供者透過他們供應的資訊,扭曲人們對世界的看法,則造成更普遍的影響。談到風險和機率,我們的大腦往往尋求膚淺的線索。這的確是個事實。這些線索大體上取決於我們產生什麼樣的情緒,或者我們心裡容易想到的事情。
這表示理性思考和風險規避幾乎沒有關係。理性思考所做的大部分事情,似乎在於把某種邏輯硬套到個人行為上,使行為合理化。
人天生不會從歷史學習。我們有足夠的線索,相信人類的天賦不利於以文化的方式移轉經驗,而是透過選擇具備某些有利特質的人去移轉。有句老話說,孩子只會從自身的錯誤中學習﹔只有自己的手燙傷,才不會去摸發燙的火爐﹔別人再怎麼警告,他們也不會小心。大人也有這樣的情形。
事情總是在發生之後,才看得比較清楚。當你回頭看過去,過去總是已經確定,因為只觀察到發生一件事。我們的心智在解讀大部分事件時,心裡想的不是以前的事件,而是用於後來發生的事件。
心理學家把由於知道後來的資訊,而高估自己在事件發生時所知道的事,稱作事後諸葛偏誤,也就是「我早就知道會這樣」。這種事後諸葛偏誤的一個更邪惡的影響,是長於預測過去的那些人,也認為自己長於預測未來,而且對於自己做這件事的能力滿懷信心。
生物學家雅克.莫諾數十年前嘆道,每個人都相信自己是進化專家(金融市場其實也沒有兩樣)。現在情況變得更糟。許多業餘人士相信植物和動物只會單向變得更加完美。把這個觀念用到社會上,他們相信,由於競爭(以及需要每季發表財務報告),公司和組織只會變得更好,不會逆轉。最強者將生存,最弱者會滅絕。至於投資人和交易人,他們相信,讓他們彼此競爭,最優秀的會大放異彩,最差的只好去學新的一技之長(例如到加油站打工,或者有時是當牙醫)。
情況並沒有那麼簡單。我們將忽視達爾文的觀念遭到濫用的基本情形,因為事實上,組織並不會像大自然的活生物那樣繁殖——達爾文的觀念是用來談繁殖的適應性,不是談生存的適應性。問題出在隨機性,這和本書提到的其他每件事一樣。
除此之外,當隨機性的形貌改變,例如發生狀態轉換,情況可能變得更叫人驚訝。一個系統的所有特質,變得讓觀察者難以辨識,就叫狀態轉換。達爾文的適應性適用於很長時間內發展的物種,短期內觀察不到——時間加總消除了隨機性的不少影響;就像人們所說的,長期而言,不同的事情(我覺得就是雜訊)會互相抵消。
由於突然發生的稀有事件,我們不是活在事物連續不斷,往改善的方向「趨同」的世界中。
生命中的各種事情,也不是以連續不斷的方式變動。我們的科學文化根深抵固地相信事情是連續變化的,直到二十世紀初才改變。
略懂隨機性問題的人,相信一種動物一定最能適應當時的狀況。其實進化論不是這個意思;平均起來,動物會適應環境,但不是每一隻動物都能適應,而且不是時時都能適應。一隻動物有可能因為牠的樣本路徑很幸運而生存下來。依據同樣的道理,某個行業「最好的」操作者可能來自一小群操作者,他們因為過度適應某一樣本路徑而生存下來——這條樣本路徑沒有遭遇進化的稀有事件影響,這裡面有個討厭的特質:這些動物愈久不曾遭遇稀有事件,他們愈顯得脆弱。如果將時間無限延長,那麼依據遍歷性推斷,那個稀有事件肯定會發生——於是物種會滅絕:進化的意思是說只適應一個時間序列,而不是適應所有可能環境的平均值。
我們可能以太過寬鬆或者太過嚴格的方式,接受過去的資訊,以預測未來。我一向懷疑這種作法,沒辦法接受單以過去的一個時間序列,作為未來績效的指標﹔我需要遠比資料多的東西。
經濟學家羅伯˙盧卡斯認為,如果人是有理性的,那麼理性會促使他們從過去研判出可用以預測未來的型態,並且採取因應行動,因此過去的資訊在預測未來時將完全沒有用處。
蘇格蘭哲學家休謨在他寫的《人性論》中,以下述方式探討這個問題:看到白天鵝的次數再怎麼多,我們也沒辦法推論所有的天鵝都是白的,但是只要看到一隻黑天鵝,就足以推翻那個結論。
培根主張不要在幾無實證成果的情形下,「結成學習蜘蛛網」(使得科學像神學)。由於培根的影響,科學轉為強調實證觀察。問題是,如果不用適當的方法,實證觀察會引導你走上岔路歧途。休謨警告我們不要接受這樣的知識,並且強調收集和解讀知識時,需要抱持嚴謹的態度--這稱作認識論(epistemology)。
人的記憶是一台專做歸納推論的大機器,想想看什麼事情容易記憶:有因果關係的事情容易記憶。
因為這麼一來,我們的大腦只要做較少的事情,就能保有資訊。體積會比較小。
歸納到底是什麼?歸納是指從許多特例中理出通則來。這會十分便利,因為通則在人的記憶中占用的空間遠低於一群特例。壓縮的結果,是被察覺的隨機程度降低。
哲學家帕斯卡表示,人的最佳策略,是相信上帝存在。如果上帝真的存在,那麼相信的人會得到獎賞。如果祂不存在,相信的人不會有什麼損失。
人們已經習慣使用QWERTY的鍵盤打字,積習難改。就像演員竄紅成為大明星,人們也喜歡採用別人愛用的方法。強要某個程序以合理的方式執行,反而多餘、不必要、不可能辦到。這稱作路徑相依結果,阻礙了我們建立行為模式的許多數學嘗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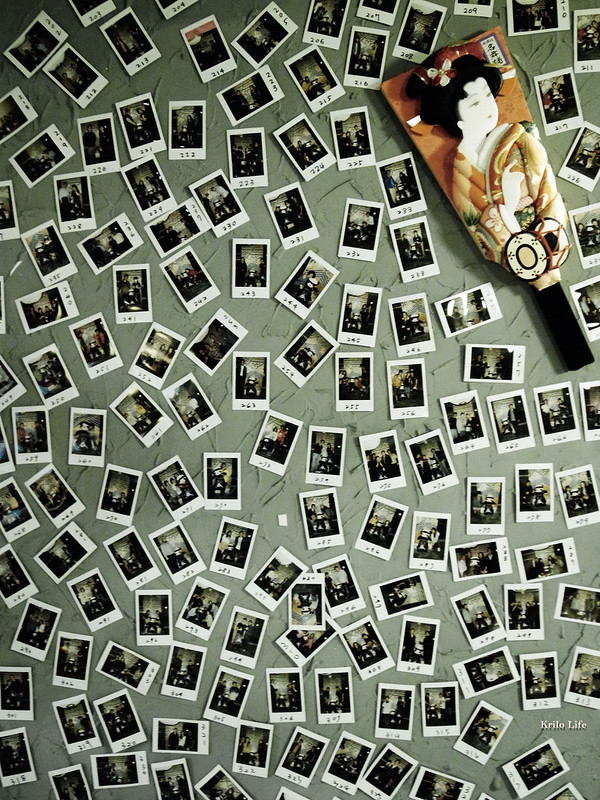
留言